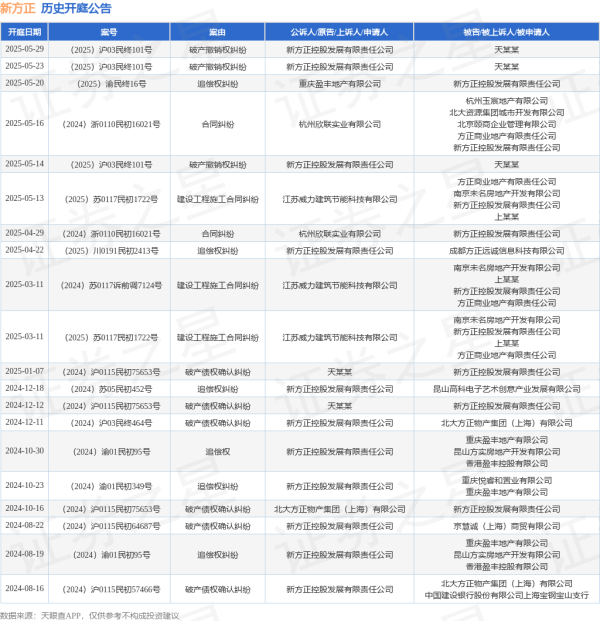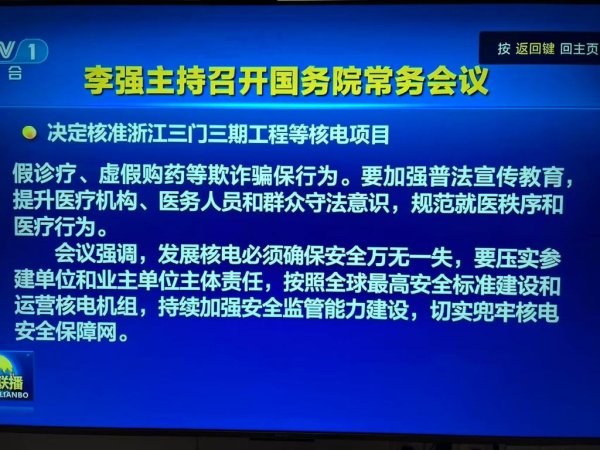1989年深秋配资网上炒股配资,我的“老兵饭店”终于开张了。
凌晨四点,我就站在了空荡荡的堂屋里。三十张铺着崭新塑料布的圆桌,一百二十把折叠椅,墙面雪白,正中挂着一幅我自己写的字——“山河依旧”。后厨飘出大骨头熬汤的香气,混着刚拖过的水泥地那股潮湿的土腥味。我,李俊,一个离开部队整一年的退伍兵,今天要当老板了。
我摸了摸左边空荡荡的袖管,那里习惯性地微微卷起,别着一枚暗红色的领章。心里不是踏实,而是一种悬在半空的恍惚。一年了,我好像还没完全学会怎么当一个老百姓。
“俊哥!”一声带着河南梆子味儿的吼叫撞破了清晨的寂静。
我浑身一震,猛地转身。门口,一个铁塔般的汉子,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,风尘仆仆,脚下是个巨大的蛇皮袋。他黑红的脸上,皱纹笑得挤成了一团。
“大牛!李大牛!”我的喉咙瞬间就哽住了。
展开剩余90%大牛把蛇皮袋往地上一撴,发出沉闷的响声,几步冲过来,不是握手,而是用他那双能抡大锤的胳膊,结结实实地给了我一个拥抱,拳头在我后背上捶得咚咚响。“可算找到了!你这地方,让俺好找!”
“你……你小子怎么来了?”我声音发颤,“从河南过来,这得……”
“爬火车呗!”大牛咧着嘴,露出一口白牙,“还能咋来?你李俊开饭店,俺能不来?看看,俺给你带啥了!”他弯腰扯开蛇皮袋,里面是沾着泥土的花生,红彤彤的山楂,还有几十个染着红点的白面馒头。“俺娘让带的,说给你添添喜气!”
我看着他,看着那满满一袋子的心意,眼眶猛地一热,赶紧别过头去,使劲眨了眨眼。“好,好……”除了这个字,我再说不出别的。
大牛是跟我一个班的兄弟,力气最大,饭量也最大,战场上,他背着我,在炮火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三里地。
还没等我把大牛带来的东西归置好,门外又响起了脚步声。这一次,是两个人。
“报告连长!王强,张小海,前来报到!”声音依旧带着军人的干脆。
我抬头,看见王强和小海并肩站在门口。王强瘦高,穿着件蓝色的确良衬衣,胳肢窝下还夹着个公文包,脸上带着点局促。小海还是那副娃娃脸,笑嘻嘻的,只是眼角也添了风霜。
“强子!小海!”我迎上去,胸口那股热流又在翻涌。
王强走上前,轻轻抱了我一下,低声说:“俊哥,我请了三天假,从厂里赶来的。”他从前是我们连的“秀才”,心眼细。
小海则递过来一个网兜,里面是两瓶玻璃瓶的桔子汽水,瓶身上还凝着水珠。“俊哥,没啥好带的,路上渴了跟强子喝的,给你留了两瓶。”
我接过那带着凉意的汽水,瓶身的水珠沾湿了我的手指。就这么点凉意,却像滚油一样烫着我的心。大牛是从地里刨食来的,强子和小海是从紧巴巴的工资里抠出路费来的。我李俊,何德何能……
“来了就好,来了就好……”我反复说着,把他们往里让。
堂屋里终于有了人气。大牛不用招呼,自己就钻到后厨,嚷嚷着要帮我剁骨头。强子放下公文包,挽起袖子就开始帮我擦那些其实已经很干净的桌子,动作一丝不苟。小海则里里外外地转,嘴里不停地夸:“俊哥,这地方真不赖!亮堂!”
我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,看着他们身上那褪不掉的军人印记,看着这间因为他们的到来而瞬间充满了“兵味儿”的饭店,那股悬空的感觉,忽然就落到了实处。
然而,这只是开始。
快到中午时,门外变得异常热闹。我正和大牛他们说着话,就听见各种口音、各种声调,混杂着惊喜的呼喊和沉重的脚步声,潮水般涌来。
“李俊!是这儿不?” “连长!我们来了!” “好家伙,这招牌,老兵饭店!够气派!”
我猛地站起身,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,疾步冲到门口。
然后,我愣住了。
饭店门口,黑压压地站满了人。一眼望去,怕是有三四十个。他们穿着各异,有的像大牛一样还套着旧军装,有的穿着工装,有的是一身朴素的农民打扮。他们年龄相仿,脸上都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,但眼睛里,却燃烧着同一种炽热的光。他们肩上扛着、手里提着各式各样的东西:用麻绳捆扎的纸箱,鼓鼓囊囊的编织袋,甚至还有拎着活鸡活鸭的……
时间,在那一刻仿佛凝固了。阳光斜斜地照下来,勾勒出他们一张张熟悉又略带陌生的面孔。那些在战火硝烟中被熏黑的脸,那些在猫耳洞里互相依偎的脸,那些在退伍告别时泪流满面的脸……此刻,全都汇聚在这里,汇聚在我这间小小的饭店门口。
我的目光从一张张脸上扫过。 那是“老班长”赵建国,他比从前更瘦了,鬓角已经有了白发,但腰板依旧挺得笔直。 那是“猴子”孙胜,他还是那么精瘦,眼睛里闪着机灵的光。 那是“大胡子”刘震,他的大胡子剃掉了,下巴显得光溜溜的,有点滑稽。 那是“秀才”王强和“娃娃脸”小海,他们站在人群里,和我一样,看着这景象,张着嘴,说不出话。 那是“机枪手”大牛,他搓着手,咧着嘴,看着越来越多的战友,激动得像个孩子。 还有好多,好多……我甚至来不及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。
他们是怎么来的?从祖国的四面八方——东北的林海雪原,西北的黄土高坡,江南的水乡小镇,西南的连绵群山……他们是怎么知道消息的?我仅仅在给有限的几个战友写信时提过一句啊!这年头,没有手机,电话都是稀罕物,他们是靠着口口相传,靠着几经辗转的信件,靠着一种我无法想象的执着,找到了这里。
他们带来的,哪里是礼物啊。那是他们各自家乡的风土,是他们能拿出的最珍贵的心意,是沉甸甸的、压得我灵魂都在颤抖的战友情。
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声:“敬礼!”
刹那间,门口所有的嘈杂声消失了。这三四十条汉子,无论高矮胖瘦,无论此刻身穿什么衣服,动作整齐划一,如同一个人。他们挺起胸膛,双脚并拢,右手五指并拢,迅速地举到额际。没有军衔,没有军装,但这个军礼,却比任何一次操练都更加标准,更加庄重,凝聚着穿越了生死、又经历了别离后全部的情感。
阳光照在他们举起的手臂上,仿佛一道无声的闪电,劈开了我所有的伪装和坚强。
我站在门槛内,看着这片举起的手臂森林,看着这一张张风霜满面却眼神灼热的脸。胸口那股压抑了整整一年的,混合着失落、迷茫、挣扎和硬撑的堤坝,在这一声“敬礼”和这片手臂森林面前,轰然倒塌。
泪水,毫无征兆地奔涌而出。不是默默地流,是决堤,是滂沱。我张着嘴,却发不出任何声音,只有肩膀无法控制地剧烈抖动。我用那仅存的右手,死死捂住眼睛,可滚烫的泪水还是从指缝里疯狂溢出,顺着脸颊,流进嘴里,又咸又涩。
一年了。退伍这一年,我像个没了魂的躯壳。我学着做生意,赔光了安置费;我学着跟人打交道,却总显得格格不入;我装着一切都好,装着适应了这个社会,只有在深夜,摸着冰冷的断臂,才知道自己心里缺了多大一块。我告诉自己不能哭,我是个男人,是个连长,哪怕连队没了,我也不能垮。
可此刻,在这群生死兄弟面前,我所有的坚强都土崩瓦解。我不是什么连长,不是什么老板,我只是李俊,一个在他们面前,可以脆弱,可以流泪的李俊。
大牛第一个冲上来,用他那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的大手,胡乱地给我擦着眼泪,自己的眼圈却也红了:“俊哥,哭啥!高兴!咱高兴啊!” 强子也走过来,用力握住我的右肩,声音低沉:“俊哥,我们都在。” 小海带着哭音喊:“连长,我们都想你啊!” 老班长走上前,他没有说话,只是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,紧紧握住了我的右手,重重地摇了三下。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我使劲点着头,泪水还是止不住。我甩开大牛的手,用袖子狠狠抹了把脸,努力想挤出一个笑容,结果表情肯定比哭还难看。
“进……进来!”我哽咽着,侧身让开,“都他妈给我进来!外面站着像什么话!”
兄弟们哄笑着,涌了进来。原本空荡的堂屋,瞬间被塞得满满当当。椅子不够坐了,后来的人就干脆站着,或者几个人挤一条长凳。喧闹声、笑声、互相捶打胸膛的声音,几乎要把屋顶掀翻。
大牛不用吩咐,直接钻进后厨,操起两把菜刀,咚咚咚地开始剁肉馅,那架势活像在阵地上拼刺刀。强子和小海成了临时指挥,安排着后来的人找地方坐。几个兄弟自发地去后厨帮忙洗菜、生火。女眷们——几个跟着来的战友媳妇,也笑着挽起袖子,开始剥蒜、摘菜。整个饭店,像一个突然被注入灵魂的机器,轰隆隆地、充满生机地运转起来。
我看着这混乱而温暖的场面,心口的暖流几乎要溢出来。我走到那幅“山河依旧”的字下面,默默地站了一会儿。
开饭了。桌子上摆得满满当当。大盆的红烧肉,油光锃亮;整只的白切鸡,金黄诱人;碧绿的炒青菜,堆得像小山;还有兄弟们带来的各式家乡菜——东北的酸菜粉条,湖南的腊肉,四川的泡菜……中间是两大盆热气腾腾的饺子,白胖胖的,像一群可爱的元宝。
没有酒杯,就用饭碗倒上白酒。我端起一碗酒,站到堂屋中间,所有的喧闹立刻安静下来。几十双眼睛都注视着我。
我深吸一口气,看着这一张张亲爱的面孔,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。 “兄弟们,”我的声音还是有些沙哑,“我李俊……没想到……今天能来这么多人。” 我顿了顿,努力平复激动的心情。 “一年了。我卸了领章帽徽,回了老家。说实话,这一年,我过得……不踏实。总觉得心里头,空了一大块。夜里有时候醒来,还以为在猫耳洞里,听着外面的动静。” 许多兄弟的眼神黯淡下去,默默点头。 “直到今天,看到你们!”我的声音陡然提高,带着泪,也带着笑,“看到你们站在门口,看到你们给我敬礼!我他妈的才知道,我那一块,没丢!它就在你们这儿!在每一个兄弟这儿!” “咱们的连队,番号没了,可咱们这些人,散不了!咱们的情谊,黄不了!” “别的都不说了!”我高高举起酒碗,“这第一碗酒,敬咱们那些……没能回来的兄弟!” 说完,我弯腰,将碗里的酒,缓缓地、庄重地洒在地上。
所有人都站了起来,沉默着,将碗中的酒洒在地上。堂屋里弥漫着浓烈的酒香和一种肃穆的哀思。
我重新倒上一碗酒,再次举起。 “这第二碗,敬你们!敬翻山越岭来看我李俊的每一位兄弟!干!” “干!”三四十条喉咙同时迸发出怒吼,声震屋瓦。所有人仰头,将辛辣的白酒一饮而尽。
酒一下肚,气氛彻底热烈起来。兄弟们开始互相敬酒,回忆着当年的糗事,叫着彼此的外号。 “猴子,还记得你偷连长的烟,被罚扫了一个月厕所不?” “大胡子,你那胡子呢?咋成小白脸了?” “秀才,别光顾着吃,给大家整两句诗啊!” 笑声、闹声、吹牛声,此起彼伏。
大牛端着一海碗饺子,蹲在我旁边,吃得呼噜作响,一边吃一边说:“俊哥,你这饺子,馅儿调得真香!比咱炊事班老马强!” 老班长端着酒碗过来,跟我碰了一下,低声问:“手,还习惯吗?” 我摇摇头,又点点头:“慢慢习惯了。” 他叹口气:“都一样。刚回去那阵,我半夜总惊醒,我媳妇都说我魔怔了。慢慢来,会好的。” 强子也过来了,他酒量浅,脸上已经红了,他看着这热闹的场面,喃喃道:“真好,就像……就像又回咱们连队过年了一样……”
我看着他们,看着这满屋子的人,心里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力量填满。是啊,就像回了家。有兄弟在,哪里都是家。
夕阳西下,金色的余晖透过窗户,洒在杯盘狼藉的桌子上,洒在每一个带着醉意和满足的脸上。分别的时刻终究还是到了。
兄弟们互相搀扶着,在饭店门口道别。没有过多的言语,只是用力地拥抱,重重地拍打对方的背。 “保重!” “常来信!” “下次到我那儿去!”
我站在门口,一个个送别他们。大牛红着眼睛,一步三回头。强子和小海跟我用力握手。老班长又对我敬了一个礼……
终于,人都散尽了。喧闹了一天的饭店,重归寂静。只剩下满屋的桌椅,空气中残留的饭菜香和酒气,以及那无比充盈的、温暖的气息。
大牛和强子、小海留了下来,帮我收拾残局。我们谁也没说话,只是默默地擦桌子,扫地,洗碗。配合默契,仿佛还在连队里做着例行的工作。
收拾停当,我们四人坐在门口的石阶上。秋夜的风带着凉意,吹在脸上很舒服。远处,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。
“俊哥,”小海轻声说,“你这饭店,以后就是咱们的据点了。” “对!”大牛瓮声瓮气地说,“谁要是敢来这儿捣乱,俺第一个不答应!” 强子笑了笑,没说话,只是递给我一支烟,帮我点上。
我深吸一口烟,看着袅袅升起的青色烟雾,融入深沉的夜色里。左边空荡荡的袖管,在夜风中轻轻晃动,但我的心,却不再感到空虚和寒冷。那里被一种更坚实、更厚重的东西填满了——那是穿越了炮火硝烟,超越了时间和距离,在今天被彻底唤醒和印证的情谊。
山河或许依旧,人间几度春秋。但有些东西,永远不会改变。
我望着战友们离去的方向,虽然早已不见他们的身影,但我知道,他们就在那里,在祖国的四面八方。而我这间小小的“老兵饭店”,今晚之后,将不再只是一间谋生的铺面。
它是我们共同的锚地,是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,更是我们这群老兵,散是满天星,聚是一团火的配资网上炒股配资,永远的家。
发布于:陕西省联丰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